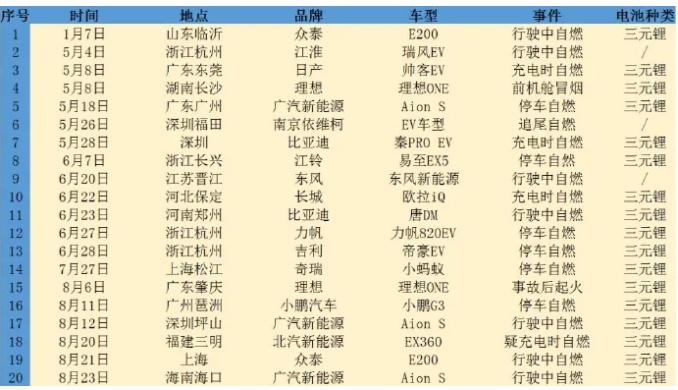长城的多手布局,氢燃料电池车量产在即
 全球范围内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的趋势不可逆,而一直以来凭借零污染、可再生、加氢快、续航足等优势,氢燃料电池技术在理论层面上完爆石油与锂电池,也常常看看做车用能源的「终极形式」。
全球范围内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的趋势不可逆,而一直以来凭借零污染、可再生、加氢快、续航足等优势,氢燃料电池技术在理论层面上完爆石油与锂电池,也常常看看做车用能源的「终极形式」。
但美中不足的是,氢燃料电池技术的产业化进度一直很慢,迟迟无法落地,对于氢能利用的「远景」,也是一直被规划,但迟迟没量产。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锂电池技术及产业化的突飞猛进,氢燃料电池技术被过度轻视。而最近一两年,氢燃料电池又重新引起了注意,原因之一就是纯电动车遇到了两个硬核问题:
续航卡在下一代锂电池技术突破和能量密度卡在物理化学的极限,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氢能源才被中国国家再次重视起来,日本、德国和中国,其实都没有放弃氢能源研发。
相关企业更进也比较迅速,比如丰田、宝马都在持续研发氢能,而在中国长城汽车也在持续不断更进,但具体氢能是否具备技术落地的可行性,以及在研发过程中的难点在哪。我们对此采访了长城汽车未势能源总裁陈雪松。
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氢能源燃料电池为什么在我国的发展不如纯电动和混动车?
陈雪松:在整个交通和能源领域里,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和公司说是单一路线走到底的,都是随着技术的演变战略不一样。在中国氢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能总是从技术、经济性方面考虑,还要考虑战略能源安全和环境治理,未来减碳要达到目标等因素。种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氢能方面会有大发展,这次《能源法》拟将氢能列入能源范畴,也是从国家的层面传递这么个信息。
问:近三年来,长城在氢能技术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雪松:刚才也提到长城做氢能从 2016 年立项,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迅速建立了国际化团队,有40多位外籍专家、近百人的研发团队,同时决定投入建立氢能研发中心。经过四年多的投入和科技的攻关,现在是时候公开讨论一些了。
成绩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1、氢能业务已经完成了全球发展的产业布局和初步产业链的建设,在保定建立了国际化的研发中心拥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拥有了360余项专利。
2、拥有开发高性价比燃料电池发电机和储氢产品的整个开发体系平台。研发投入有 12.3亿,目前上公告的有两款发动机,一个是 97 kW 大功率用于商用车,还有 65 kW 用在大巴车、物流车方面的;乘用车方面,现在有 95 kW 和 80 kW,燃料电池乘用车会在2021年进行小批量示范。
3、零部件供应商水平、规模缺乏,为了满足目标,长城很多核心零部件都是自己开发,比如说用高速的空气轴承的空压机、氢循环泵、还有升压器、电堆等。目前已经开发出了系列产品,比如说大功率的电堆满足发动机的要求有100kW、120kW和140kW,并且是金属版的高功率密度、大功率电堆。
而电堆核心零部件,比如说技术双极板膜电极也有研发团队,有自己的试制线,自动化产线可以每年产100万片膜电极,满足大致3000辆的规模。同时也有电堆1000台套的自动化产线,已经投入使用了,现在装载的电堆都是产线上下来的堆。
除了发电还有车载储氢,我们自己搞的也是比较先进的70MPa和35MPa III型和IV型氢瓶,瓶阀和减压阀以及集成的车载储氢系统,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车上要用的,已经开发出来装到乘用车上路上试了。
问: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仍有一些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被外国公司垄断,面对封锁,长城汽车如何突围?
陈雪松:现在所谓的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瓶颈是电堆,空压机是最明显的,此前一款空压机得花几十万,现在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瓶颈了。已经有了发动机以及匹配该功率的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搭载在车上在试了。
而瓶颈是后期的问题,比如说规模化生产:
1.质量怎么保证; 2.成本怎么降下来?目前国内行业还是没有到那个阶段,这个行业核心零部件供应,现在还没有产能,有的是在规划,这可能需要时间去进行验证。
现在不管谁做,包括长城,从材料级别确实是有瓶颈的,因为像电堆里面用的三大核心材料,催化剂、质子膜和碳纸也有一些国内厂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可以供样品。
但是,如果装载在车上的要求从质量稳定性和性能上还达不到。
但也有一个作用,是这些国产材料会迫使进口材料的价格迅速下降,就像空压机一样。因为国内有了供应,国外的供应商就不敢漫天要价,不会把利润定在200%、300%。
问:「人才储备」是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石,能否介绍一下长城汽车氢能研究目前的研发团队?
第二个问题,提到氢能源燃料电池的成本控制,长城觉得最主要是哪个方面?是催化剂的重金属用料降低,还是整个电堆在大规模投产之后通过规模经济效益缩减成本?
陈雪松:截止到 7 月相关总人数已经接近 400 人,专家超过了50人。
我们战略规划根据 DOE 模型,结合中国市场做过预测。DOE 的假设那些条件都成立,只要扩大规模,成本就可以下降大约是 92%。我们根据中国的数据和政策、企业、技术进行预测,靠规模效应成本下降幅度可能会达到 58% 左右,剩下的还得是靠技术进步。
丰田曾经提出一个降本的路线,要靠技术的进步占比 75%,规模只能占 25%,技术进步一方面意味着单位体积、重量材料产生的电力要多;另外是不是可以借助材料改良,比如催化剂不用铂,一下子成本降了很多。
从这两个方面去看,我们认为中国现在如果是靠规模的话是能起到一定的降本作用,但是这还不够,还得必须要进行技术的创新才能够真正达到没有补贴后大规模商业化的成本目标,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材料的研发一般都要 5 到 10 年,因为要从材料级别、零部件级别、系统级别、整车级别逐层进行验证。工程可能是两三年的产品开发周期,长城也在做一些规模化的投入,自己有产线,会比供应商的成本低一些,至少是从成品率、效率这些方面有竞争力。分析下来单靠规模达不到商业化竞争的水平,比如说 1kW 对应 500 块钱靠规模是达不到的。
问:安全是发展的重中之重,请问长城汽车如何保证氢能研发、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陈雪松:主要从两方面考虑:
1.从企业经营方面入手,怎么样能够保证经营场所的安全;
2.从产品设计角度、产品应用方面如何保证安全。
比如说,分三级氢安全管理系统,逐级进行管控;采用的设备也是有一定安全方面的考虑,整个设备的水电气怎么样隔离、探测,怎么样跟整个建筑进行报警通风紧急应对等等。
另外在操作方面也要有严格的操作规范,要有流程,比如做一个实验,首先要对实验进行危险源的识别,针对每个危险源是不是有解决方案,我们叫做「未分析不操作」。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非常严格的安全要求。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对于功能安全、电气安全、碰撞安全、氢能安全是经过严格的分析进行设计。
1.在设计上要有冗余,要有非常高的安全系数,对于各种失模式进行充分的分析,并且要制定企业标准,企业标准是要严格高于行业标准,因为行业标准是按照平均水平定的。
2.制作过程中要有严格的质量监控,不仅设计的安全性要高,还要防止制作过程中质量控制不好、检验指标不到位,在这过程中也要进行安全的考察。
问:刚刚聊到长城汽车在氢能源方面高度自研,有近 400 人的专家团队,请问长城汽车目前的氢能发展遇到哪些困难?我们是怎么解决它的?
陈雪松:目前遇到的有些困难是行业内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加氢难、用氢贵、用车成本高之类。
除了这些还有我们某些技术产品是有前瞻性的,所以在产品进行市场推广和寻找用户的时候遇到行业标准不存在、法规不允许等问题。
举个例子,我们研发的70MPa的塑料内胆,我们管它叫IV型瓶,它具有重量轻、成本低的优势,实际上在国外早已经商业化了,但是在中国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产品在真正车辆推出的时候遇到了很特殊的困难。
还有低温液氢的技术,但目前液氢只允许军方用,民用还没有开放。
问:长城汽车的技术进展,燃料电池寿命、效率、低温启动、催化剂铂的用量有没有详细的数据可以提供?我们的产品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陈雪松:催化剂的用量都在减少,现在催化剂的用量都是按照每平方厘米多少毫克,长城现在可以做到 0.35。
从效率来说,每平方厘米我们现在可以产 1.3 W。
从冷启动方面,从电堆的角度已经是验证了零下负 30 度启动,储存零下 40 度是没问题的。
问:氢燃料电池未来 5-10 年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长城氢燃料电池车辆有哪些?第二个问题,长城测试车辆跑的场景有没有相关数据,在安全性这一块。